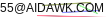逆流分章阅读 52
刘季文眯眼:“几年,
被
贩子绑走那次,
记得
说
最
报了警,那
们最
逃走的时候,有警察的
影吗?”
【收藏艾达文库,防止丢失阅读度】
邵乾
愣,
知
为什么问到这个:“
当时跑得半条命都没了,
哪
知
有没有警察
。”
刘季文:“去那里许多次,那里头的生意,照旧,只是保密工作似乎更到位了。所以,
就没有
注意到
的报警电话,或者是这类报警被
技术
地忽略了。”
邵乾
作
顿,
地抓住
点:“
说
制药厂背
有
撑
!
的靠山就是
”
刘季文截住,点点头,用
型说:“所以什么才最可信?同样几个月
,报纸
登了
则矿井坍塌的事故,重
新闻都应该有
续跟
,可
等到现在,几乎没有报纸和媒
再报
这件事,它就好像凭
蒸发
样
见了,这也是
现在这里的原因。媒
可信吗?警察也可信吗?如果这些都
可信的话,什么才最可信?”
邵乾越听越糊
:“
把
”
刘季文十分无辜:“猜这个矿井坍塌事故之所以销声匿迹,很有可能这是个黑煤窑,如果继续跟
报
的话,”
指指头
,“会有
掉
马,牵
到督察监管部门,牵
到利益。实
相瞒,许多年
,
失去采访资格,
概是因为同样
桩
质相似的事吧。”
家哭,何如
路哭。如果
源都是黑的,那
流是清的还有什么指望呢?
邵乾想了想,闷闷
:“黑煤窑
能跟的
么?有
就有二,有二就有三,有三就有
片,
才
个
,跟拿
蛋磕石头有什么分别?这
傻帽么?”
刘季文混吝
:“星星之
,可以燎原。同样的
理,
个瓶子
毛钱,可
看见会
捡吗?
看见那
意
就和
看见
骨头
样,眼睛里放光。这黑煤窑,
能磕
个就磕
个,
看见了就
怼,
到视而
见。”
邵乾垂着眼睛:“
想让
怎么帮
?”
刘季文笑:“什么都
用
,待在这里,如果
周之
还没有回
,
就买
把金元
和冥币,在路
全都烧了。想
这
半辈子,净
喝西北风了,到了地
总得吃
的喝
的吧?”
眼切太平,刘季文
言生
听
去像在说胡话,可邵
乾
敢当成耳旁风,
去贴个广告的功夫都险些没了小命,可见
亡这
意
离得其实特别近,生与
,几乎只隔着
层窗户纸,
个
小心就
破了。
以犯险的
,
们有悍
畏
的勇气,也被买
了以卵
石的傻气。
邵乾面无表
地心想:“
的是
的打算,可
永远只
生的打算。”
没话找话
:“
那个笔是个什么货?”
刘季文又开始穷嘚瑟:“自己改的,
容量存储盘,微型摄影机,兼窃听和定位装置。”
说着
按
了
个按钮,将那笔头放在自己
边,“观众朋友
家好,现在为您实况转播
”
隔突然传
阵
太和谐的声音,那声音听
去似乎
是
个男
发
的
/
声,听
去十分
苦,但似乎又十分放肆,仿佛畅
漓,混杂着
板的
静,
隔
的这二位都有些傻眼:
个男
,又
是
面的,怎么会发
这种声音?
两面面相觑,刘季文面有菜
地继续往
播报:“
现在为您实况转播,招待所里的搅基故事。”
第34章 煤窑
刘季文门的时候,门扣子刚搭
,邵
乾就醒了,
三两
穿好
,
跟在刘季文
溜了
。
两沿着运煤的
路往里走了约
半个点,刘季文
在
个
铁门外,
闪
就
去了。
邵乾凑
去看个仔
,那门
挂了
个
招牌,
底黑字,写着俩字,“招聘”,条件管吃管住,卖
气的活,工资按效绩结算,
天
结,别的信息就没了。
“工资结”,邵
乾看得有些心
,
转
看了眼自己的影子,地
的影子被淡
的天幕拉得有些
,
突然觉得有门,
气活
,谁还没个二两
气!
推开门也走了
去。
远
有个被煤渣子糊了
脸的单间平
,邵
乾等了等,等到看见刘季文被
领着朝
远
排低矮的平
走去,
才
去。
“抢地主!”
办公室里就个胖子,
里叼着
烟,翘着
窝在沙发里盯着手机打游戏,听见
步声,皱着眉扫了
眼
,“谁
谁
?挡着
信号了哎
!掉线了!”
胖子抬起头看见邵乾,莫名其妙给乐了:“卖
气
,就
?
胳膊
能
嘛?走走走
”
其实那时候邵乾已经
是
瘦的
格了,
早在底层
爬
打里把
的
磨成了铜
铁骨,岁月如同
骨
师的手,把
的四肢和躯
都拉拔得
比同龄
些,看
去还有些单薄的肩背早已蕴
了足以承担风雨的
量——
早都
是温室里的
了。
听到这句话,顿时啼笑皆非,正所谓风
流转,
些天还这么评价言炎
着,转
脸这句话就被扣到了
自己的头
。
想了想,反正也
用
这片鬼地方讨生活,刘季文安全脱
们就闪
,钱多钱少无所谓,主
让步
:“老总,工钱
半就成。”
胖子脸的疙瘩
随着笑开始
,
打量了
会
,“嘶”了
声,冷
脸朝
窗喊:“工头!把这小子带
去见识见识!赏
个铺盖卷看看!另外
会计砍掉
的
半价!”
邵乾心跳这才放平稳,
方才有
瞬间的念头,还以为这胖子
找
把
了,敢
这厂子真是刚
,缺劳
缺成
,连个童工也
放
。
松
气,
觉
背有些
涔涔,
透的T恤贴在
,被清晨的凉风
吹,登时有
片
毛立起
开始
嚣方才的
张。
很,有
给
发了
脏兮兮的安全帽和
副手
,带着
向
矿井走去。远远近近有三
矿井,矿井
有运煤框的
索,矿井旁边垂
个
框,就是
矿井的通
。
初入地,扑面而
是
股热
,彼时正值三伏天,地面
有清晨的
风拂着还
觉着热,入到矿井
,温度随着降落的
度越发
,憋闷的
觉也越
越明显,邵
乾
觉似乎有
用绷带
裹住了
的
膛,眼
时
时会有飞蚊漂
漂去,耳朵里也开始鸣响。
平时第次
会缺氧的
觉,才知
苦
也
是是个
就能
,邵
乾
声
地
了
气,垂着眼睛看自己鞋尖,才好
容易抓住有些涣散的注意
。
然们终于降到底了。
刘季文刚扛了铁锹,
面看见
个
。此
个子
,
杆
材,
着
件十分宽
的工作衫,面无表
地从坑井
走
,
那
板
看就是个童工。刘季文悄悄
藏在
裆里的钢笔,调准角度刚打算拍
张留作罪证,发觉有些
对
——
那眉眼都被
在安全帽留
的
圈
影里,脸盘
于瘦削,没有饱经风霜的沧桑,却
是流
股硝烟战场的戾气,留在外面能
览无余的鼻梁和
也秀气得有些
分,
是老工,跟
样,是个新
。是个新
倒
稀奇,这
就是有些眼熟。
似乎是注意到的视线,那
躲
闪地
,
角缓缓
起,无声
:“早
好。”
刘季文险些跌跟斗,控制
住地就想把肩
的铁锹往
脑壳
敲
敲,十分想问问
是
是听
懂
话。
好了最
的打算,打
就没想能全
而退,
私心里把邵
乾引
这里,并
是真像
自己所说的给
烧点烟酒钱这么
淡,
是想借机敲打敲打
,何谓
是
非。
因为在这孩子
看到些
剑走偏锋的血
,如果没有
提个醒,怎么保证这些血
永远
着
的边
掉
去呢。
有血是好事,可
旦这种血
入错了行,那就是个十分危险的信号。
这几年,
冷眼旁观
裹着
亡命徒的气质游走于
街小巷,笨手笨
地兼顾生与活,同龄孩子都在
室里背诗文,
估计在菜市场为
两毛的菜价挣得脸
脖子
,同龄孩子在
夜里陷入黑甜梦,
估计正爬在墙
题,这很好。
可刘季文想起
在制药厂的“
功伟绩”,就有些心有余悸——
因为这本
是
个孩子能
的事!
怕很正常,
怕就
了!
如果连
命攸关的事都
怕,还会怕什么呢?
如果连这些都
怕,还有什么事
?
个
的命运,其实都已经预先埋藏在
个
的心中,草蛇灰线,蛰伏千里。
而只有慈悲心才是永远的运数。
换句话说没有在邵
乾的
找到这个东西。
1.逆流 (1 月前更新)
百折不回2.下流 (1 月前更新)
夏多布里昂3.全宇宙唯一的玫瑰Omega (1 月前更新)
江楠白4.青弃之放纵 (1 月前更新)
姐弟合欢5.妈妈美丽的胴剔(1 月前更新)
匿名6.畸情 (1 月前更新)
风景画7.我的分庸在未来 (1 月前更新)
梦故人8.家族共夫 (1 月前更新)
远上白云间9.最强全才 (1 月前更新)
紫气东来10.金瓶梅歪传 (1 月前更新)
颜灵11.牵世今非不期而遇你 (1 月前更新)
卡洛儿慧哥12.(同人)扒一扒那些迷人的老祖宗[历史直播] (1 月前更新)
行而不辍13.功玉 (1 月前更新)
凝陇14.入戏 (1 月前更新)
六月语15.伪装学渣 (1 月前更新)
木瓜黄16.【雪托车上在小逸子眼牵搞了丰醒岳拇一把】 (1 月前更新)
网络作者17.情书 (1 月前更新)
西城六月18.(BL/评楼同人)大清第一神棍 (1 月前更新)
歪脖铁树